手術失敗後中風的逆轉奇蹟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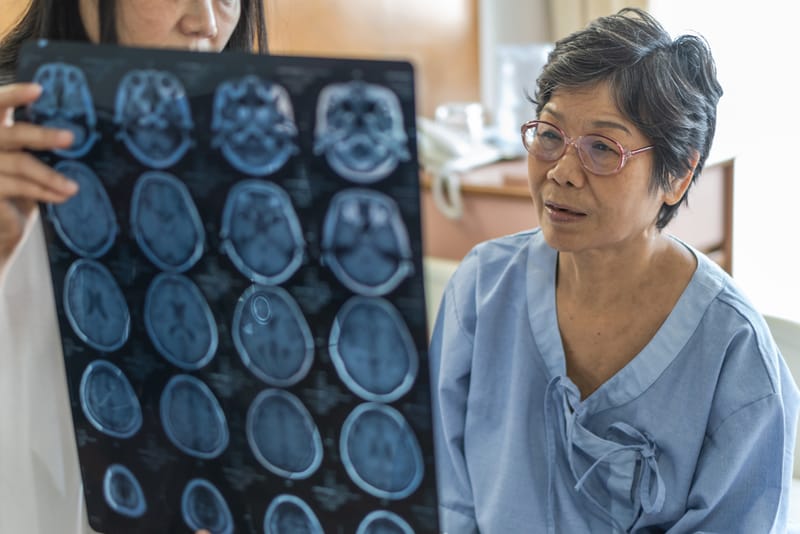
六十多歲男子手術失敗後中風逆轉篇
《從 95% 的希望跌入絕望,再到奇蹟甦醒》
命運的反轉
去年,一位六十多歲的男士因頸動脈嚴重阻塞,被安排到大型醫院接受頸動脈支架及成形手術。這類手術成功率高達 95%,術後通常兩三天即可出院,本應是一場「例行而安全」的預防中風措施。
然而,命運卻在這裡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——手術後,他不僅沒有如期康復,反而成了中風的受害者。
在香港,這樣的故事並非孤例。每天都有病人因為心血管問題接受手術。醫生口中的「高成功率」,對家屬來說或許是一種安慰,但當那 5% 的風險真的落在自己身上時,數字瞬間失去了意義。對妻子而言,這不是統計學,而是她眼前最親近的人,正在生死邊緣掙扎。
妻子的煎熬:從希望到絕望
根據妻子後來的描述,手術結束後的時間,像被拉長成沒有盡頭的長廊。她坐在病房外,腦中一遍又一遍閃過同樣的問題:
如果他醒不過來,我要怎麼辦?
如果他就這樣昏迷一個月、兩個月,甚至更久呢?
如果他真的離開了呢?
她猛地抬手輕敲自己的額頭,像要把這些念頭趕出去,低聲告訴自己:「不可以想這些,要冷靜。」
然而,腦海依然亂成一團:要不要找中醫會診?哪位醫師值得信任?該不該聯絡朋友或親戚?每一個念頭都像一條岔路,卻沒有一條是清晰的。她想抓住一個方向,卻發現自己根本無法專注,像被困在霧裡,分不清哪一步才是對的。每一個假設都像一把刀,慢慢割在心上。外表看似安靜,內心卻早已翻江倒海。
甦醒後,他被轉送至腦科病房,但情況並沒有好轉:
無法活動
無法言語
眼睛無法睜開
無法進食、喝水
大小便完全失控
她回憶起醫生曾經提到,兩年前也有過一宗相似的案例。她急切追問:「那位病人後來怎樣了?」醫生沉默片刻,才無奈地說:「他幾天後就離世了。」這句話像一盆冷水澆下,徹底擊碎了她心中僅存的希望。她腦中閃過一個念頭——難道丈夫也會走上同樣的結局?
憤怒與無助交織,她忍不住在心裡質問:為什麼手術前說成功率這麼高?為什麼沒有提醒可能會出現這樣的後果?是不是醫生過於自信,甚至忽略了某些細節?她的情緒在那一刻徹底崩潰,既害怕失去丈夫,又對醫療團隊充滿怨懟。
醫生束手無策,只能觀察。她守在床邊,眼神緊盯著他蒼白的臉,手不時輕輕握緊他的手,彷彿這樣就能把力量傳過去。走廊的每一聲腳步,都讓她猛地抬起頭,眼裡閃過一絲希望,但下一秒又落空。
這是一段無聲的煎熬——時間被拉長,心卻一點一點被掏空。
黃金康復期的嘗試
家屬聯絡我時,已是病情的關鍵時刻。為了把握黃金康復期,我在首七天內,每日利用兩節探病時間,親自在病房為他進行氣場重塑,以祈禱作掩飾,避免打擾。家屬同時提議,她全程陪伴,並代為應對護士或其他人的干擾。
然而,第一次的療癒,卻讓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挑戰。整整一小時,我竭盡所能地嘗試各種手法,希望能刺激他的身體機能,但他卻毫無反應,彷彿陷入了沉睡。我感覺到在身體層面上,有一股頑固的阻力,像是一層厚厚的屏障,阻礙著血液循環和神經傳導,讓療癒的效果難以顯現。
那種感覺,就像試圖喚醒一棵枯萎的樹木,無論我如何澆灌,都無法讓它重新煥發生機。我能感受到他肌肉的僵硬和緊繃,以及身體深處的虛弱和疲憊。這些生理上的阻礙,就像一道道無形的牆,阻擋著療癒的進程,也阻礙著他的康復。
我開始反思,是否我的方法不夠精準?是否我忽略了某些重要的細節?但看著他緊閉的雙眼和毫無反應的表情,我知道我不能輕易放棄。我必須更加仔細地觀察他的身體狀況,調整我的手法,找到突破這層阻礙的方法。
我深吸一口氣,閉上眼睛,仔細回想著之前學過的各種技巧和理論。我試圖從生理學的角度,分析他身體的狀況。我能感受到他身體的能量流動非常微弱,許多穴位都處於閉塞狀態。
我決定調整我的策略,從疏通經絡、活絡氣血入手,試圖喚醒他身體的自我修復能力。我更加輕柔地按摩他的肌肉,刺激他的穴位,並配合呼吸的調整,希望能幫助他放鬆身心,促進血液循環。
第一次的挫敗,像一記重拳,狠狠地擊中了我。但它也像一盞明燈,照亮了我前進的方向。我知道,這是一場漫長而艱辛的戰役,但我絕不會退縮。因為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病人,更是一個需要幫助的親人,一個渴望重生的靈魂。我將用我的知識、我的耐心、我的愛,一點一滴地融化他身上的冰霜,幫助他重新找回生命的活力。這不僅僅是一份工作,更是一份承諾,一份永不放棄的誓言。
當晚第二次進行時,只剩下儀器規律的滴答聲,像是時間流逝的低語。第一次的挫敗並未讓我氣餒,反而更加堅定了我的決心。我再次將雙手懸於他的頭部與胸前之間,全神貫注地微調能量的流動,感受著他身體微弱的脈動。
就在我全神貫注之際,奇蹟,在寂靜中悄然發生。他的喉嚨忽然微微顫動,像是沉睡的火山即將爆發。我屏住呼吸,不敢錯過任何細微的變化。下一瞬間,一個極輕、極弱,卻清晰的聲音,如同破土而出的嫩芽,從他口中溢出——兩個簡短的字。那聲音沙啞、咬字不清,但在術後多日的沉默之後,卻宛如一道光,劃破漫長而黑暗的長夜。
那兩個字,輕得幾乎聽不見,卻重如千鈞,撼動了整個病房。
據家屬回憶,當他第一次在沉默多日後吐出那兩個模糊的字時,妻子整個人僵住了。她凝視著他,仿佛時間都停止了流動。那一刻,她明白,這不只是聲音,而是希望的回歸,是生命力的重新燃燒。她先是愣住,眼睛睜大,難以置信地看著他,隨即眼眶迅速泛紅,淚水奪眶而出,嘴唇顫抖著喊出一句:「他說話了!」聲音中,既有驚喜,又有釋放,更有對未來重生的期盼。
那一刻,我知道,所有的努力都值得了。即使前路漫漫,充滿未知,但只要有一絲希望的光芒,我們就絕不放棄。因為拯救的不是一個人,而是一個家庭,甚至日後他的康復或許能夠影響其他的同路人。
情緒失控與約束措施
最初,他昏迷不醒,或是進展緩慢,意識尚未完全恢復,對外界刺激幾乎沒有反應,更談不上任何掙扎或抵抗。我們小心翼翼地照護著他,期盼著奇蹟的出現。然而,隨著病人的狀況一天天好轉,意識逐漸清晰,他開始強烈表達想要離開醫院的意願。長期臥床的束縛,讓他對自由的渴望與日俱增。
醫生對他恢復得如此迅速感到困惑,態度也變得謹慎甚至有些不安。或許是擔心病情反覆,又或許是對超出預期的進展感到難以掌控。病人因為渴望自由,加上對醫院環境的厭倦,情緒逐漸急躁,時常對護士大聲吼叫,甚至不顧自身安全,堅持要自己下床行走。
最終,護士依照醫管局的臨床指引,為了避免病人可能傷害自己或他人,採取了「身體約束」措施——將他用繩索固定在病床上。這種做法在醫院屬於標準程序,目的是保護病人與醫護人員的安全,但對病人而言卻是一種強烈的刺激。曾經的無力與順從,如今被限制與束縛所取代,他因此更加憤怒,甚至開始對醫生和護士產生敵意。妻子多次嘗試解釋與安撫,希望他能理解醫護人員的苦衷,並配合治療,卻收效甚微。看著他被束縛在病床上,痛苦掙扎的模樣,妻子心如刀割,卻又無能為力。
醫生對康復神速的迷思
病人太太回憶起手術當天,早上進行的手術,按理說下午就應該結束,但時間一分一秒過去,直到傍晚五六點,仍不見病人出來。她和家人開始焦慮不安,四處詢問護士,但得到的總是含糊其辭的回應,似乎大家都知道發生了什麼,卻又欲言又止,只叫他們耐心等待。直到當晚,病人終於穩定下來,被送往加護病房,醫生才神情凝重地向她坦白,手術過程出現了意外,病人一度情況危急,經過長時間的搶救才得以脫險。醫生解釋,由於當時情況瞬息萬變,無法預測結果,所以才沒有及時告知。那種漫長的等待、無助的猜測,以及得知真相後的震驚,與現在病人逐漸康復的喜悅,形成了強烈的對比。
作為氣場重塑的執行者,我能感受到病人身上能量的變化,以及他因此而產生的積極反應。但我並未將這些直接告知醫生,畢竟,這並非主流醫學所能理解的範疇。
或許,醫生也注意到了病人超出常規的進展,但他選擇以一種更為謹慎的方式觀察。他或許在思考,這種快速康復的原因是什麼?是病人自身的潛力?是更有效的復健方法?還是…其他未知的因素?
我能感受到,醫生對此抱持著一種既好奇又懷疑的態度。他或許無法解釋這種現象,但他並未完全否定。他只是選擇以一種更為科學、更為理性的方式,去思考、去記錄、去分析。 所以才堅持病人需繼續留院觀察,他知道,有些事情,並非科學所能完全解釋。而我,則默默地在另一條路上努力著,運用氣場重塑的方式,為他提供著輔助。至於這份輔助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,現階段或許難以用醫學標準來量化,但病人的進步,卻是真實可見的。
我深信,這一切的背後還有其他無形的力量在加持,而我所做的,只是其中微小的一環,更重要的是,全靠病人自己的自癒能力,我只是從旁協助激活那股原本殘餘的自癒能力,才慢慢進展到今天有較好的現況。
我的介入與安撫
根據病人的太太多次觀察,只要當我一走進病房內,病人原本那股躁動不安,往往會奇蹟般地慢慢消散。我究竟做了什麼,能讓他如此安心?而我又將如何運用這份信任,為他爭取更好的治療?
他緊皺的眉頭,總在我踏入病房的那一刻舒展開來。原本煩躁地抓著床單的手,也慢慢鬆開,彷彿找到了停靠的港灣。我輕聲地問他:「今天感覺怎麼樣?」他只是微微點頭,眼神卻充滿了感激。我知道,這份信任,是我最大的力量。
我安撫他的情緒,並非只是為了讓他安靜。我更想利用這份平靜,為他爭取更多的時間和機會。我建議妻子向醫生提出專業評估,這不僅是為了給醫生施加壓力,更是為了讓醫療團隊真正看到他的進步,為他爭取提早出院的可能。
只要我在,他就能感受到那份安定的力量,我深知我的氣場不知不覺地影響了他,在中風復健的道路上,時間就是生命。每一天,每一刻,都至關重要。所以,我繼續握緊他的手,輕聲地對他說:「別怕,有我在。」因為我知道,我的介入與安撫,不僅能平復他的情緒,更能為他帶來希望,點亮他前進的道路。
醫院環境的隱憂
事實上,在我持續療癒二十天後,我已經感覺到這個環境對他並不利。醫院裡人來人往,氣息沉重,許多故事在這裡開始,也在這裡結束。雖然我不便明說,但我能感受到一種不易言喻的壓力與沉重,長期停留並非最佳選擇。
這段時間裡,我親眼見過隔壁床的病人離世,家屬哭喊的聲音久久迴盪不散;也見過新送來的重症患者,腦部嚴重受創,情緒混亂,整個病房的氛圍因此變得更加壓抑。這些場景對一般人來說已經難以承受,更何況是正在康復中的病人。
或許很多人也曾聽過親友分享過類似的經歷——醫院裡除了病痛,還有一些看不見卻能讓人心神不寧的東西。病人因為身體虛弱,往往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抵抗這些外在的氛圍與能量,情緒和狀態很容易受到牽動。正因如此,我更希望他能早日離開,回到一個更輕盈、更有利於康復的環境。
一步步的復甦
接下來的日子,他像沿著一條看不見的山路往上走,每一天都有一點點新風景浮現:
初覺醒:左腳腳趾微微抽動,像有人在遠方輕敲門。
感覺回潮:皮膚對觸碰的反應變明顯,冰熱刺激能分辨,痛覺不再遲鈍。
目光追隨:能用眼睛緩慢追著家屬的手指或手機燈移動,偶爾會主動找尋聲音的來源。
呼吸穩定:呼吸節奏由急促轉為均勻,胸腹式呼吸逐漸協調,夜裡不再頻繁驚醒。
吞嚥重啟:喉部反射回來,能吞下一小口水,從濕棉棒到勺餵,再到少量流質飲食。
簡單指令:聽懂並完成「眨兩下眼」「握握手」「抬抬腳」等單一步驟指令。
四肢覺醒順序:左手開始能輕握,右腳能屈伸,右手能抬離床面,活動範圍一日比一日大。
關節鬆解:肩肘腕、髖膝踝逐一恢復活動度,被動帶動到主動配合,痙攣逐步減輕。
腿部水腫開始減:原本緊繃腫脹的小腿與腳踝逐漸消腫,皮膚顏色恢復正常,活動時不再明顯沉重。
精細動作:手指能捏起綿球、按遙控器、滑手機螢幕,從顫抖到逐漸穩定。
語音回歸:先是母音與單字,接著能說短句,發音含糊轉為清晰,可表達基本需求。
理解與表達(據家屬描述):能聽懂並正確回答日常生活中的具體問題,例如家屬問:「你住哪裡?」他會清楚地說出完整地址;問:「幾樓?」他能立刻回答「五樓」;再問:「二叔的電話是多少?」他會一個數字一個數字地報出來。剛開始時,他的回答常常錯漏百出,有時地址說不完整、樓層記錯、電話號碼順序顛倒。但家屬每天都用同樣的問題反覆練習,像在腦中一點點鋪路。幾天後,錯誤逐漸減少,到後期幾乎每次都能答對,與第一次相比,進步之大令人驚喜。